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(修訂一版) | 做自己 - 2024年11月

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(修訂一版)
完整一個現代臺北市的出現,並非人口增加、市地擴張的「自然」結果,而是現代權力在空間上運作的「社會」產物。清代的傳統治理 「看不見」擁有獨特意義的「地方」;日治時代的現代治理則從根拆解地方的原有意義,從而「看得見」每塊空無意義的「空間」。清末到日治的社會變遷深沉而複雜,透過臺北現代都市空間的出現,似乎可以窺見現代社會(modern society)的登臺之路。
在這條現代空間之路,地方情感已被剝除,任何空間皆可停泊,但也將不再久留。這是易於流動的「空間」,易於看穿、易於監視、易於穿越,卻不是可以積累生命意義的「地方」。
此乃是條不可逆也不可擋的旅程,但活在現代空間裡的我們,終究仍須省思如何會走到這樣的時代。現代化未必是什麼好字眼;推動現代化也未必是值得禮讚的事。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、現代都市空間的出現,只是在說明臺北有過這樣一個美麗的汙名。
本書特色
臺灣政府自2009年以來,在徵地與都市更新問題上搞得輿論譁然、眾怒難平。相較於清朝末年當官的含糊敷衍、委曲求全,當前的政府看似展現了點兒現代國家的權威,但辦法拙劣、手段粗暴,比起縝密算計、操作細膩的日本殖民政府可謂望塵莫及。當然,本書可不只是國家(政府)權力如何施用於人民的操作說明,更可作為人民理解國家施為本質以便應對進退的教戰手冊。
作者簡介
蘇碩斌
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,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,曾任教世新大學社心系。學術專長為文化、都市、休閒、媒介等領域,著有《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》,譯有《基礎社會學》(合譯)、《媒介文化論》、《博覽會的政治學》(合譯)。
自序
第1章 尋找現代臺北的系譜從不是地方說起:臺北地名意義的變遷三個市街如何變成一個都市?
第2章 臺北三市街的偶然與必然1 漢人社會浮現:荷鄭及清初的北臺灣2 第一個市街:艋舺搶走八里和新莊地位3 第二個市街:大稻埕攀進世界茶葉市場4 第三個市街:城內與國家積極統治
第3章 不透明的清末地方社會1 誰在支配地方?紳商才是力量2 市街紳商國家與地方之間的折衝3 模糊統治原理:看不見摸不著的人與地4 清末科學建設:新思維陷在舊社會
第4章 穿透臺北的日治空間工程1 空間即權力:殖民加現代的統治原則2 地方社會弱化:傳統仕紳的分化與質變3 均質化的推動:警察制度掃除中介的勢力4 視覺化的起始:公共衛生與市街貫通
第5章 現代都市空間的成立1 數目字管理的權力:生物統治與調查統計2 土地調查與地圖:土地統治的知識系統3 戶口調查與統計:人物統治的知識系統4 精準計畫非偶然:1905年及1932年的治理性
第6章 空間不是自然而是社會流動性與公共性的出現縱貫全島、迎向世界的臺北在均質性之中製造新的異質性過去的那個臺北啊
附錄1 清代臺灣地方行政體制演變附錄2 日治時期臺灣地方行政體制演變附錄3 日本歷任臺灣總督及民政長官之任期附錄4 1932年臺北市六十四町及十九村落位置及人口結構(依日本人比率由低至高排序)
參考書目人名索引事項索引圖片一覽表格一覽
自序
聽吹過臺北的風聲 蘇碩斌
I 學海無涯!既然無涯,就永遠登不了彼岸,想來就覺得很累。因此在學海優游或漂流,總須設定暫時停泊的港。作品,無非就是暫停以告別過去的港。《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》這個作品,原本也只是一個暫停的港,我未料竟爾三次造訪,也未料每次造訪都有驚喜的靈光。
2002年臺大社會學系博士論文《近代臺北都市空間之出現》, 是作品的初次成稿。當我把博士論文送進蝸居一整年的圖書館上架,想說任務已經終了。2005年應社大文庫之邀改寫,經過刪減篇幅及簡化理論後由左岸出版,以《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》為名在書店上架,是作品的第二個面貌。可惜社大文庫與左岸的版權合約無法維續,社大知我盼望絕版多時的著作重出,乃建議另覓出版管道。幸得群學劉總編輯不計舊書重印的銷售風險慨允改版,才有作品的第三個面貌。
本版《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》出版緣由,簡要即是如此。雖因承襲舊稿而未大幅更動書寫架構,不過本版花費頗多心力改正先前生澀寫作留下的疏漏,另也重繪圖表和重訂標題,希望在這個暫停的港口留下美好的身影。
作品三度呈現的期間,鐘錶時間走過了八年,我的就職機構更換過兩次,生活世界卻也逐漸多方為難。總覺得自己彷若學術鐵軌上一輛每站必停的貨運車,不斷卸載教學、寫作、發表、審稿、開會、談話、輔導的貨包,一心駛向虛幻的終點。為了應付定期的學術考核,就得求取速效的研究成果,不時也感嘆是否已成為Max Weber訕笑的「自以為登上世界頂峰的無靈魂專家」。然而我仍無力棄離所屬的學院軌道,只能期許以書寫的有血有淚獲得讀者的共感共應。
這樣說來,改版其實是因為更強烈的情感因素。2005年《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》出版後,除了熟識的學界友人捎來意見,素昧平生的讀者竟如入夜繁星點點浮現,不僅熱切指正錯誤、交換感受,甚至提供寫作材料助我補充論證。
地理遠闊卻心理相近的人們,在靜默的書物中感受彼此的存在,體會彼此的渴望,既是思想共同體,也是情感磁力場。這才是重新出版的最大誘惑啊!
II 作為一名長期的社會學學徒,我始終想要探問一個社會學的基本問題:我們的社會怎麼會是今天這個樣子?在我的研究領域中,我試著以「現代空間的誕生」為討論的依據,在本書則化身「臺北如何由前現代進入現代」的問題外形。臺北進入現代的時點,恰是清末自強與日本殖民的轉折之間,因此在時局詭譎滄桑的臺灣當代,這個問題不僅是學術疑雲,也是政治賽局。
為此,我常被問及為何未著力批判殖民暴力。我也試著回答,陳述歷史現象,其實就是陳述歷史觀點。選擇以現代來解讀臺北,而不選擇以殖民來解讀臺北,都只是研究者的歷史觀點。凡人不可能是宇宙的全知,學者也不可能是觀點的全知。凡人學者寫作的歷史敘事,當然有觀點的局限;反過來說,以一己觀點寫作的歷史,無非就是邀請朋友聽我講故事。覺得我的見解有意思,何妨帶著趣味當作故事一讀;畢竟歷史已經過去,人間已不可能確定唯一的真實。
我不是學院嚴格訓練的歷史學者,即使有心遵循傅斯年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、動手動腳找東西」的名訓,但長時期的社會學思緒,仍覺得歷史事件並不理所當然,也堅信解釋材料需要理論刀鋒。我懵懂讀過Max Weber、Georg Simmel、Walter Benjamin、Henri Lefebvre、Michel Foucault,感受到理論刀鋒為史料劈出了令人驚奇的觀看蹊徑,從而領略到「現代」是人類社會最優雅的暴力。我想,如果放棄將「現代」視為直線演化論者誤認的「進步」,閱讀歷史的心情必可更加深沉。
本書無非是在陳述「現代∕空間」如何優雅且暴力的現身。臺北何時進入現代的問題,這樣看或許比較清醒,擁有回首來時路的感傷心情就足夠,不須陷溺在為了「水龍頭普世價值」爭功諉過的狂熱中。因為一切只不過是跟著西方登上名為現代的黑船、航在不能回頭的汪洋罷了。
III 有幸活在資訊通達的年代,更加深刻明白知識沉澱的可貴。資訊不是知識,就像把研究材料依序編排只會成為電話簿而非巨著。因此,我必須由衷感謝師長及前輩的引領及共讀,這才是知識世代相傳的重要成因。指導教授章英華及葉啟政兩位老師,啟發我重估歷史的深刻思維,終身受用不在言下。博士論文承蒙張維安、張茂桂、溫振華、陳東升諸位委員的斧正,求學期間深受伊慶春、孫中興、顧忠華等師長的授業鼓勵,無一不在開啟學問的眼界。顧忠華老師當年推薦這本論文到社大文庫,更是我學術人生的重要一步。特別要提及日文導師吳滄瑜先生,十年前不知所以踏進吳老師的補習班,幸賴相互督促的同學鄭陸霖一路同行,才有幸持續蒙受吳老師無私的指導,不僅得以參詳日文資料,更藉此連結今村仁司、吉見俊哉、若林幹夫等嫻熟歷史的社會學者之著作。日本比臺灣更早走在親近西方的路途,經由日本社會學來理解源起西方的現代,對我而言實在是一趟滿載收穫的思想奇旅。
我還必須感謝一起研讀理論思想的重要夥伴。當年寫就一本論文時,尚猶是初淺的空間生產批判,後來又與黃厚銘、汪睿祥等友人幾年間研讀Jean Baudrillard的象徵交換理論,循線連上其師Henri 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,隨後在葉啟政老師的世新讀書會中,才又發現這些沿襲Emile Durkheim晚期思想的法國左派如何苦尋現代悲劇的出路。不斷研讀西方思維,是為了設法離開西方支配,我很慶幸沿途總是有驚喜,也確認沒有錯看空間背後有權力,更想望住在土地上的人們都有顛覆空間的可能性。書末最後幾段隱隱提及的,無非就是這些年閱讀西方理論的感想。
還要感謝世新社心系、陽明人社院的所有夥伴,知識與情感兼備的環境,確實因為心情愉悅而想讓寫作更努力,也謝謝助理馮忠恬、曾子靈、曾馨霈和編輯沈志翰的悉心校閱,修飾了很多瑣細的缺失。再則感謝這幾年跨域學界友人的交流,施懿琳、李承機、呂紹理、李育霖、黃宗儀、張文薰等師友對本書的評述與指教,大大增加我回頭修改的動力。當然更要謝謝家人的相陪,際遇無常的人生總有一處穩當的地方。最後要向那些讓我看見歷史的機緣致謝。一個人會看見過去,總是因為一種機緣而在一處位置看到一些事兒。機緣是個開端,然後關心的事兒會愈來愈多,體驗與感觸也會愈加豐富。我當初投身臺北市街研究,原本只是打算作一名躲在圖書館拼湊地圖文獻的紙上作業員,幾次耐不住獨坐書桌的寂寥,才開始穿梭在寫作的地景之間,也開始愛戀地方的一切。這種心情,或就用Antoine de Saint-Exupery的《小王子》一書中狐狸對小王子的表白來比擬,也為曾經在此停泊的機緣做一個註腳:
看吧,你看見那邊的麥田嗎?我並不吃麵包,麥子對我一樣也沒有用處。那些麥田並不會使我想起什麼,這倒有點傷心。但是你有金色的頭髮。於是當你馴養了我,這將是很好的一件事!那些金色的黃小麥,將使我想起你,而我將喜歡聽吹過麥田的風聲……。
是的,我將喜歡聽吹過這片土地的風聲。
第1章 尋找現代臺北的系譜昭和四年(1929年)8月19日,廣播節目放送著一名男子的聲音,飄過他正談論的都市上空:這個都市位在平原,東西南北各方都有充分擴張的餘地……,現在,綠蔭、道路、上下水道、電氣設施,都大略整理過了,民宅家屋的外觀,也已經統一改正,路樹豐茂,市容不雜沓也不喧囂,既清潔又明亮,都市面積不過大也不致狹小,並逐步建造了官府、學校、公共設施。雖然還只是小規模都市的形態,但放眼望去,盡是令人愉快的市街。聲音的主人叫井手薰(1879-1944),是當時臺灣總督府的土木局營繕課長。當天的廣播節目主題是《臺北の都市美》,由「臺北放送局」播放,井手薰說的美麗都市當然就是臺北。他以「我覺得臺北是個好地方」作為開場白,娓娓道出對臺北過去的感受與未來的期待:以前毅然決然進行改善的臺北市,不論在市容或道路方面,至今都已小有規模,……稱得上是美麗可愛的中型都市,如果要繼續改善,還有很多向上提升的餘地,這點我很有信心。希望我們這個難得的可愛臺北市街,能夠朝向完全模範都市的理想邁進。1這段話在報刊雜誌上多次轉載,同年的《臺灣建築會誌》第1輯第4號、《臺灣時報》11月號都看得到,應該是當時最典型的臺北都市圖像。作為一名都市營建官僚,把自己管轄的臺北視為可建設、可規畫的對象,表達「大略整理過了,如果要繼續改善的話,……我很有信心」之類的話,無論是出於官場客套或真誠熱情,聽起來似乎自然而然、稀鬆平常。但臺北一直都是可建設、可規畫的「一個都市」嗎?翻開歷史,恐怕不盡然。清代治臺重臣劉銘傳在光緒十五年(1889)的一分奏摺上,如此陳述他曾費力建設的臺北:竊查臺北自光緒初年分設郡治,僅將城垣、文廟、試院、府署,陸續粗成,其餘地方工程,因民力難籌,多未興辦。……統計臺地近年貨釐、鹽茶等項,涓滴歸公,已無外銷之款,此等工款,平時原可責令紳富籌捐,惟現當清賦升科,既未便踵襲陋規,按田科派,且臺北修造城工,並法防捐助,民力已勞,地方亦形竭蹶,再四籌畫,惟有將各工物料地價銀兩據實開單,恭呈御覽,仰懇飭部立案,准令作正報銷,以昭核實(劉銘傳 1958:290-291)。劉銘傳在此是百般無奈的官員。近十年的臺北城建設,蓋了四面城牆、些許屋宇,還留有諸多工程未辦,稱不上成果斐然卻實在官民皆疲。他只求經費能夠核銷,對於都市建設的未來已不可能有什麼理想和信心。劉銘傳面對的城市範圍,只約當今天臺北市城中區面積的「臺北城內」而已,並非當代我們熟悉的臺北樣貌。清末劉銘傳建造臺北城,讓臺北呈現為「三個市街」,也就是艋舺、大稻埕、城內,井手薰建設的臺北則相對是「一個都市」的現代臺北。從地理學家陳正祥在《臺灣地誌》(1959)描繪的這張人口分布圖大致可知:「三個市街」的意義,基本上就是清朝末年在臺北盆地上形成的三個各具歷史、相互區隔、卻又毗鄰往來的地域單位。至少,由兩個年代的人口聚居圖來看(圖1.1),1895年的臺北與1920年的臺北確實很不一樣。劉銘傳的心力交瘁,迥異於井手薰的成竹在胸。一處地理位置、兩個歷史時點,何以建設都市的際遇如此歧異?答案應該無涉個人才幹,而是兩人鑲嵌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權力運作模式中。出現一個完整的臺北市,也就是現代都市空間的出現,恐怕並不「自然」,而是非常「社會」。
 太宰治必讀經典套書(人間失格+維榮...
太宰治必讀經典套書(人間失格+維榮...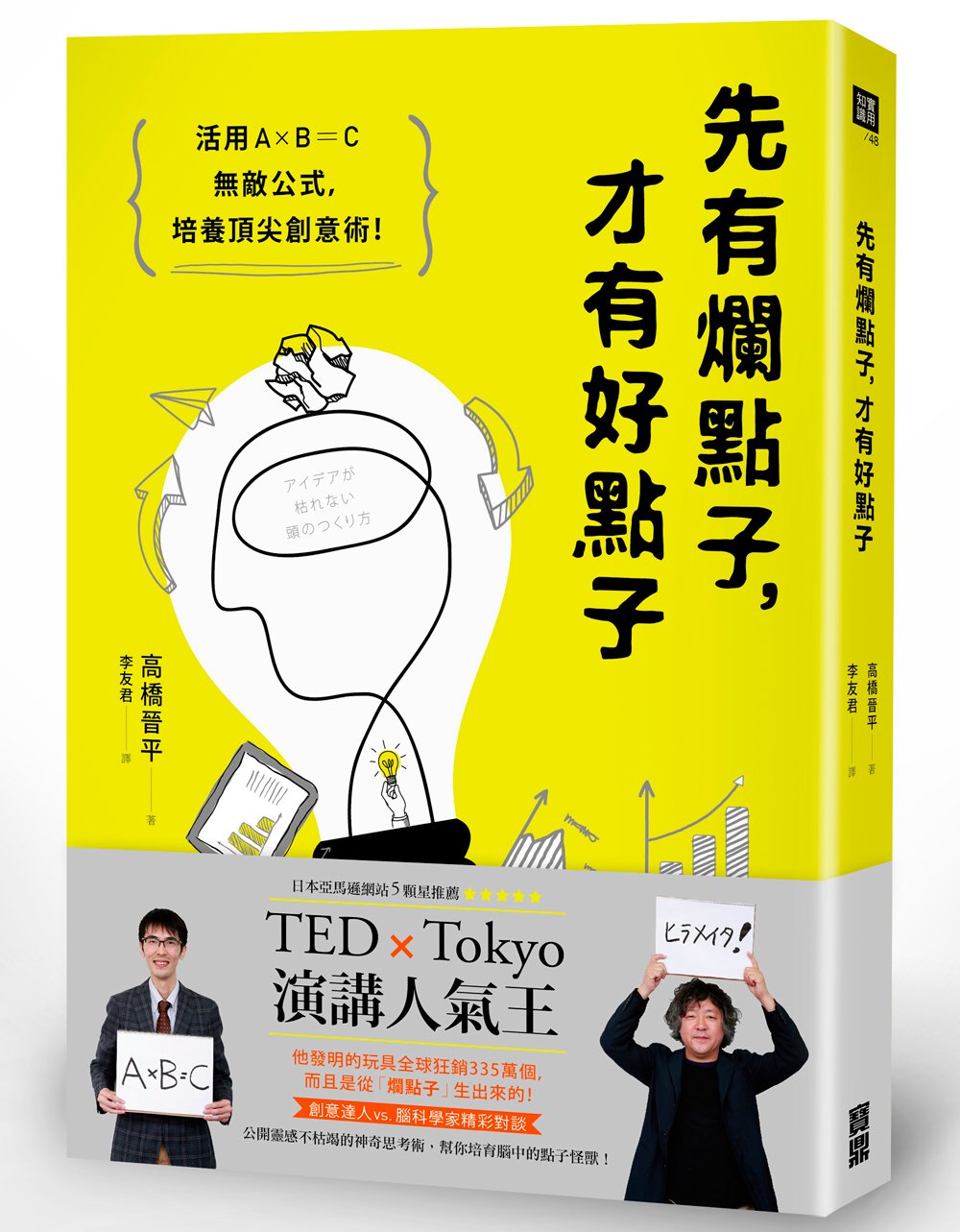 先有爛點子,才有好點子:活用A×B...
先有爛點子,才有好點子:活用A×B... LOOM MAGIC05-超吸睛的...
LOOM MAGIC05-超吸睛的... 給孩子的動畫實驗室
給孩子的動畫實驗室 秋天的森林:讀《秋夜寄邱員外》(點讀版)
秋天的森林:讀《秋夜寄邱員外》(點讀版) 繪本大師英諾桑提套書(隨套附贈:英...
繪本大師英諾桑提套書(隨套附贈:英... 知中:幸會!蘇東坡
知中:幸會!蘇東坡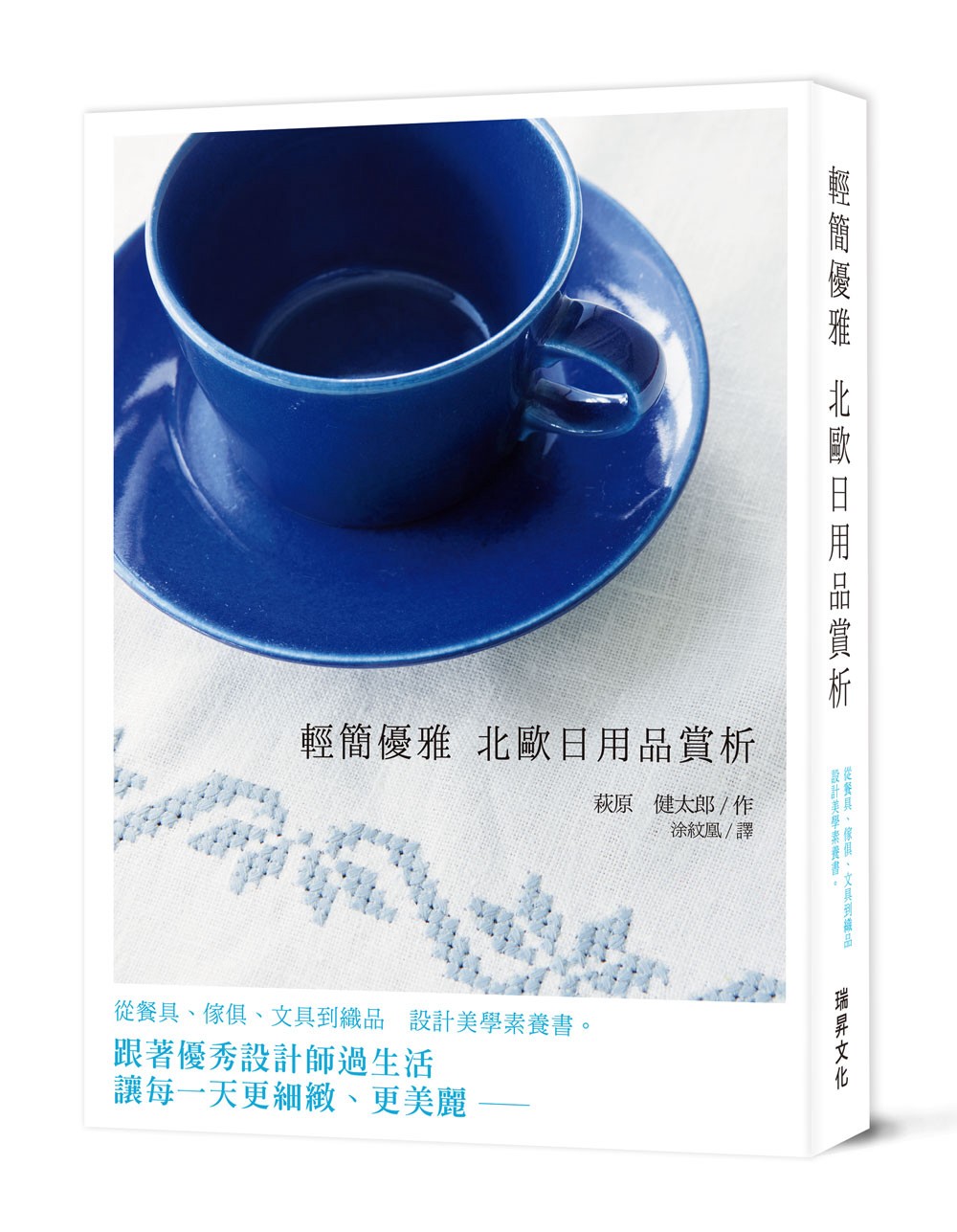 輕簡優雅 北歐日用品賞析:從餐具、...
輕簡優雅 北歐日用品賞析:從餐具、... 可愛時尚的磁鐵娃娃屋(新版)
可愛時尚的磁鐵娃娃屋(新版) 藝術,在這裡[精裝附光碟]
藝術,在這裡[精裝附光碟]